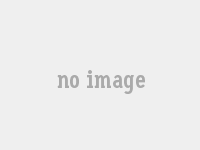家住大泽西
那是十月的某一个清晨,如红牛乳一样浓稠而洁白的大雾正笼罩着松嫩平原。四野一片宁静,空气中充满了慵懒而又有香甜的水汽。在这样的节气、这样的时辰、这样的气象中醒来的人,就算你睁大了双眼也还是难以分辨自己到底是躺在现实之中、梦境之中还是时间的深处。

不知道这场雾起自何时,又何时能够散去。似乎一切都要看草原上的风向如何,如果风向一直向西,那么来自查干湖源源不断的湿气,一直会继续把大平原深深地掩埋,就像一个吝啬的人,会花上一生的时间去埋藏他的宝藏一样。似乎连时间也会被浓雾夹裹着一直返回到很久以前或上古时期。那时,查干湖并不叫查干湖而是叫大水泊;那时,透过时光的雾霭,我们甚至随时都能够听到老鵏、天鹅和丹顶鹤那深沉如历史、高远如天空一样的鸣叫。
然而,一般情况下,风是不会向西的。这个季节,风会从南方或西南一直流向人们正在思想着或潜意识里期待着的未来。这是风,也是时间的必然走向。五个时辰之后,或许我们就能够看到大平原清晰的面容。
那时,我还没有离开故乡,仍然是查干湖湿地边缘草甸式草原上的原居民。当我在那个早晨醒来时,还没过十三岁生日。那时,我虽然也隐约听说过,在村子的东方,似乎十分遥远的地方有一个东旱河,虽然我住的房子其实离查干湖岸边只有不到十公里的路程,但我却从来不清楚东旱河就是查干湖,更不知自己就居住在古代传说的大水泊的边缘。那个年龄、那分心智和已有的见识还没有能够让我看清周围的一切。
雾已经无声地移动了它的脚步。这原本在天空中流浪,被大地的温暖和尘缘迷惑而跌落凡尘的云,以一种极其眷恋的神色,一步三回首地慢慢消隐于村庄那边的树林背后。然后,我们看到了草尖有一点发黄但却十分广阔的草原,看到了聚集在村庄周围的参差间种的农田,有一些早熟的品类已经被收割完毕,秸杆一堆堆地堆放在地垄之间,一些从果荚或果穗上脱落的子粒散落在各处的泥土之上,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烁着钻石般的光芒。
天空碧蓝如刚刚织出的一匹彩缎。有透明的风在其间穿行,像一束看不见的丝线,牵引出人们意想不到的声音和图案。
大雁总是以偶数结群,排成令人遐想的人字队列,飞在高处,一路行进,一路撒下此起彼伏的鸣叫。多年来,我始终也没能真正破解大雁鸣叫声里透出的苍凉与悲戚。但无论如何,这苦命的鸟儿,它的身影、它的声音总会让我们牵肠挂肚。
雀鹰似乎是这片草地上常驻的税务官,不论春夏秋冬,它都天天搜巡在树林与草丛
之间,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随意捉去一只山麻雀或草原鹨,就算是这一片草原向它缴纳的税金或“租子”了。
而大天鹅是轻易不肯露面的,偶尔有三五只从高空中悠然而去,给我们的感觉,总如白色的梦幻一般,轻盈而飘渺,它们不露疲态的身姿,无数次地向这里的人们暗示着一个错觉,它们洁白的羽毛永远都不会沾到泥土,他们的生活只合在天上。
在这个季节里,野鸭是不会成群结队的。偶尔,它们被突然从哪个池塘的芦苇中惊起,充其量也不过是三五只的规模,数双忙乱的翅膀频率极高地噼啪一阵乱舞,直打得银色的芦花四处飞扬,仿佛整个秋天都跟着慌乱了起来……
那些年,每当我看到拖着两条长腿的丹顶鹤在夕阳里翔过树梢;每当我看到农田里的某一积水处聚集着各种各样的水鸟,我心里都要泛起深深的疑惑。为什么我的老家,一个十年九旱的地方,会有那么多水禽或经常依水而居的鸟类来往、出没?直到后来我才发现,那些鸟儿的集散地就在不远处的查干湖上,它们在那里有大规模的活动和聚会,它们到我所居住的村庄来,就如同我去自家的后园一样方便随意、自然而然。有时,当一只孤独的斑纹鹬在干涸已久的池塘底部徘徊,神情里充满了哀伤和依恋,我一时真不知道我和那只鸟谁该是那片土地的真正主人,谁更有理由留下,谁该安静地走开。
事实上,我们看不见的,鸟儿能够看见;我们无法记清的,鸟儿们仍然记得清楚。亿万年以来,这一片湿地就是鸟儿们的领地。自从地球的造山运动把数亿年前的大湖之水从大小兴安岭以南的簸箕面儿倾入大海之后,贯穿整个松嫩平原的广大湿地生态就已经基本形成。以扎龙、萨尔图、莫莫格、向海、查干湖、大布苏等大面积低地水域为中心的草甸、水泽,向四周幅射、延展,构成了它们世代生息的家园。
后来有了人烟,有了一批多于一批闯关东的先民,有了逐渐增多、不断扩张的城市和乡村。再后来,人们在这里居住得越来越久了,就一点点忘记了湿地的历史,忘记了时间流程里的很多事情。自然的伦理、湿地上的秩序,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模糊、复杂,像不再清澈的湖水,像不再宁静的天空。
当鸟儿仍以主人的姿态光临那些庄稼时,庄稼的主人便像鸟儿一样地叫起来,噢噢地对鸟儿们发出驱逐信号。不知道以最高的声音说出来的话语,是不是就意味着真理,但很显然因为力量上的强大,人类已经成为湿地的真正主人。鸟儿们虽然往返于自己几万年一直沿袭下来的迁徙路线,但它们的正当性或正义性已经受到土地主人和钢枪的严重置疑,因为它们的翅膀之下,是大片大片正在成熟的庄稼。
假如时光就是像戴在腕上的一只手表或摆在桌上的一只闹钟,可以随意拨弄,那么我一定要冒一次时间倒错的风险,把指针拨回到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和人们共同回望查干湖湖底的大面积龟裂、瘦弱得目不忍睹的湖水以及天地之间无鸥无鸟、死寂无声的苍茫。我要和人们穿过时光的隧道共同感之,如果地球上最后只剩下了人类,而没有了湖泊、草原和湿地,或者只有湿地而没有了给土地带来动感的鸟兽在其间穿行,这世界还会有什么生机和乐趣!
所幸,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开出了新的水源,查干湖重获新生,并从本世纪初,延岸的乾安和前郭等县又全面推行了退耕种草政策,在查干湖周边的草地上大面积禁牧,人、农机以及牲畜全线从湿地向后撤退。在人们退去的地方,绿色的草线,像绿墨水在萱纸上的泅散一样,开始扩展、移动,越过那些白花花的碱地,越过牛羊践踏过的斑斑驳驳的黑土,重新抵到了农民的田地。
一场小型的洪水过后,水塘和低洼的田地里到处都有青蛙和鱼。我在久违了的故乡的土地上,再一次听见了苍鹭们低婉的歌唱。这个几乎和湿地一样古老的物种,吉祥与和顺的预言家,有骨无肉的先哲,已经优美地提起一条腿,神清气定地在湿地的某一浅水处站稳,等待着自然之神把湿地的魔轮转回到那些生机勃勃的年代。
查干湖从此一定不再寂寞了。当一只苍鹭静静地站在水里时,让人想到的是鱼;当许多只苍鹭同时沉默着站在水里的时候,让人想到的是思想,是有关水、有关湿地、有关生态的哲学。
我站在久违的故乡,向着并不遥远的那湖,翘首瞩望,心中顿生一种有一点怀旧又有一点激动的复杂情绪。穿过山重水复的漫漫行程,穿过苍苍茫茫的往昔岁月,我的脚依然又落到了大水泊的边缘,而自己也依然似在多年以前的那场雾中。不同的是,此时,我心清明,我已经知道有一种机缘如生命本身一样幽深,就算你有意逃避,它也会一路尾随而来;有一段路程命里注定,该走过的,迟早还是要走。
此时,就是眼前横陈着千万重夜幕与雾霭,我也还能看到那湖,也还是能看到它一望无边的芦苇荡;芦苇荡里衔鱼疾飞的天蓝色的翠鸟;水巷里慢悠悠行进的小木船和岸边躲在大阳伞下像长脖老等一样等待时机的垂钓者;还有激烈、壮观的放网捕鱼和骑马在草原上奔跑的牧民,一路惊起躲在草丛中午睡的鸥、雀……
郑重声明:本站所有内容均来自互联网,旨在传播更多的信息,版权为原作者所有。若有不合适的地方,请联系本站删除,邮箱:599385753@qq.com。
上一篇:花在静静的开
下一篇:古诗里秋思代表了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