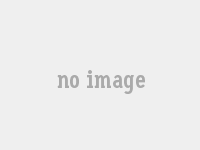童言:生活中时时距离我3米的死神
文|童言
我害怕死亡,同时又因为生命无常而慨叹。死神就像老鼠,与我们的距离从来没超过3米。
想借每日书的机会,探讨自己内心的恐惧。
命也好,运也好,死亡并不妨碍我们好好过活着的每一天。
双层巴士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广州,由于电力不足,不同区域晚间轮流停电。我家住在海珠区,排到的日子是每周一。
一到八点,一只带着白色手套的手,准时扣下电闸。窗外本来闪烁的万家灯火,如被风吹过的火光,挣扎了几口就熄灭了。我坐在客厅电视机前,还没反应过来,屏幕早已随大军溃败,留下一片茫然的空洞。
眼睛眨了眨,瞳孔极力撑开,这才重新辨认黑暗里的家具摆设。母亲摸过来,先把我安顿在沙发上,再一路摸去抽屉,哐哐铛铛翻出三两根白色蜡烛。
唰!
火柴在黑夜中破出一小个洞,母亲赶紧拿蜡烛来蹭。等烛光稳定了,母亲把新鲜融化的蜡水,倾斜倒在玻璃茶几上,蜡烛屁股趁热坐上去,顿时撑起一片小小的亮天。
“妈妈去洗澡了,你乖乖坐在这里等我出来”
我没有点头,却伸手去拉母亲。她轻轻挣脱掉,托起另一根蜡烛远去。不一会儿,洗澡房里传来哗哗水响。
我把自己抱成球状,躲在微弱而跳跃的火光中。熟悉的家此刻变得不仅陌生,还藏匿着虎视眈眈。黑暗如一只大汤勺,捅进我的身体里,把人类最原始最原始的恐惧都搅和起来。
我想到了死亡。
这个词对于一个6,7岁的孩子来说,还未能在现实中成型。但想象力像潘多拉盒子,一发不可收拾地把记忆中最可怕的镜头,都串在一起。我突然模糊意识到,再过很久,“我”这个人就不复存在了。那么,我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父亲母亲,再也没有机会坐上双层巴士了!
“哇!!!”
电力恢复于两小时后。
重新回到光明的怀抱,我把恐惧挤回盒子里,偎依着香喷喷的母亲睡觉。
停电措施后来悄然中止了,但那个夜晚的联想,如纹身,刻在脑海里。
直到现在。
自然课
在小学还未硝烟弥漫的年代,三年级课程表算得上宽裕。填上语数英音乐体育思想品德后,竟还腾出一格,留给一节叫“自然”的课。问老师这是什么?答曰:自然,不就是自然咯。
要是放在今天,这节课一定散发着青草青青的味道,甚至还可能开发成一门赚孩子钱的生意,什么户外生存技巧,什么看星星摘月亮,团购价599,扫一扫二维码即可。
但很可惜,这节课生不逢时。
每周一堂45分钟,由一位长得像某国家领导人的男老师来讲。他大概快要退休了,临享福前接受这项毫无考评压力的课。所谓“自然”,就是老师的随意,想到哪儿,讲到哪儿。漫天飞语从48只左耳朵轻轻进去,又从右耳朵轻轻出来,挥一挥手,留不下一丝记忆。
偏偏有一天,自然老师讲着讲着,突然停住了。是东西都讲完了,还是讲不下去了? 没有人知道。他翻了翻薄薄的工作本,缓慢地说:
同学们,你们关于自然有什么问题吗?我可以来试着回答。
大家都从瞌睡中醒了,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自主。黑眼睛你看看我,我望望你,最后把希望投向班长。
班长是个好学生,笔直挺起手,问了一个关于四驱车的问题。当时很多男孩都喜欢这玩意儿,问题一出来,几个车迷都抖擞了。
老师很耐心地解答,还用粉笔在干净的黑板上画了简图。班长听完后像大彻大悟,他的认可稳定了大家的军心。渐渐地,问题如雨滴,滴滴答答多了起来。
我也想提问题,但没有加入争相举手的行列。因为一来,我的问题好像比起大家的来得不一样,二来我也不敢在大家面前暴露不一样。
下课铃响了,老师在一群男生的簇拥中,从讲台挪到课室门口。我趁机凑过去,等人群都散去操场时,才轻声说出自己的疑问:
“为什么人会死?人怎么可以不死?”
老师托了托两片四方眼镜,眼镜发虚。我看得出来,他在拖延时间。
“这个嘛……" 他说,“你这个小鬼,那么怕死啊!哈哈哈哈!”
在笑声的掩护下,他摆了摆手匆匆踏上走廊。我本想继续追问,脚步刚跟上又改变主意。就让他快逃吧,我想。这个已过知天命的男人,背影宽大而无知,发黄的白衬衣上,浸出一片让人失望的汗渍。
正如他给出的答案。
下辈子投个好胎,不要再做鸡了
在肠子一样窄长的市集街道,鸡档排在蔬果贩子之后。穿过腐烂的叶子,鸡毛发骚的味道,像早上没刷牙的口气,热烘烘贴过来。
档口有三四个,每张案台都摆满白花花的鸡尸体,还有分文别类的内脏,几颗鸡心,几堆鸡胗,几串鸡肠,散发着身体的余温,像新鲜出炉的自然生物博物馆。
但广州人对鸡的要求极高,标本再新鲜也只是标本,算不上首选。最上等的,一定要眼见为实,当场杀戮。所以,鸡档一定屯有活蹦乱跳的公鸡母鸡,关在层层鸡笼子里,等候发配。
母亲领着我到达鸡笼前,还未开口,鸡佬就先发话:“要煲汤还是做白切?”
“煲汤” 母亲说。
“那挑只瘦的。”鸡佬说着,掀开鸡笼盖,手伸进去筛选。
挤满了鸡的笼子,根本没有空间逃脱。但鸡们还是嗅到了死亡来临前的味道,咕咕咕地绕着圈,尽力躲开那只不懂怜悯的手。鸡毛乱飞一阵后,一只一定是倒了霉运的鸡,被强行拽出来。鸡笼立刻恢复了宁静,大家仿佛都为躲过一劫而松了口气。
鸡佬没有给鸡留下任何反抗余地,三下两下就把一双鸡脚捆上,吊起来过称。
“两斤三两!” 他向世界宣布。
鸡倒立在另一头,仿佛已经徘徊于地狱边缘,身体不协调地抖动一下。
母亲说待会再过来取,拉着我往前买猪肉去。临走前,我听见鸡拖着嘶哑的声音,发出一声绝望的叫喊,然后,便彻底安静了。
回来付钱时,鸡已经传到鸡佬老婆的手里。她坐在地上的小板凳,用热水一遍一遍烫去鸡的毛发。脱得精光后,又传回鸡佬的刀子下。开膛破肚,五脏六腑掏出来,冲洗干净。
“鸡杂要唔要?”
“要!”
“二十二。”
母亲递上沾染过猪血的钱,拿回沾着鸡血的塑料袋,让我帮忙拿着。
我把袋子提起来,看了看僵硬的鸡爪子,又看了看笼子里眨巴眨巴的鸡眼睛,很想知道,鸡是否也和人一样,为失去同伴而悲伤。
关于鸡还有另一个故事。
乡下人不会说话,为了表达谢意,有一天把一只活生生的鸡提到我家来。
父亲抽不出空,母亲只能腾出阳台,让乡下鸡先安顿下来。也许城里没有牛粪的味道,乡下鸡在白色瓷砖上犹豫了几分钟,终于大胆迈出脚步。每天精神抖擞地在两平米的空间里游动,越走越有感觉,还下起了新鲜鸡蛋。
我们一家人自然成为最大受益者,天天吃上免费有机鸡蛋。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刚晋升为城市鸡的命不长了,就算下多少鸡蛋都救不了。周日晚宴上,缺席的主打菜白切鸡,就等着这副肉身来填补。
父亲挑了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早上,霍霍把刀磨了,还学习专业杀鸡户,准备好一盆热水来煺毛。一切就绪,母亲开始追着鸡的屁股跑。鸡那两只爪奔得快,连续让母亲扑了几个空后。最后打了个擦边球,连拽带拖地两手抓住鸡翅膀,把鸡上缴到父亲手里。
父亲两腿夹住鸡身,一手钳住鸡脖子,另一手撸开喉咙上的毛。等清晰看到鸡皮疙瘩,父亲抓起旁边的刀,把闪亮的刀刃对准目标。
“老爸!”
我喊了一声。
父亲转过头来,“做什么?”
手定格在空中。
“还是养着吧。” 我求情道,“把它当宠物。”
父亲转向母亲,母亲转向鸡,脑袋里回想起每天清洗鸡屎的乐趣,和吃下鸡蛋的温暖,最后转向我说:“好吧。”
鸡感觉到父亲的手松掉了,连忙拍着翅膀逃命。确保一切都安全后,它缩到阳台的一角。不知道是否因为感恩,鸡在这之后,每天发了疯似的下蛋,以至于我们家鸡蛋,从冰箱溢至厨房,客厅,甚至爷爷奶奶家里。全家人在庆幸营养充足的同时,也感激这只名正言顺的城市鸡。
一年半后的一个早晨,我还在睡觉,父亲过来推醒我,带来一个沉重的消息:
鸡快要不行了。
我连忙爬起来,看到鸡已被安放在一个鞋盒里,全身蜷着,眼睛困得睁不开眼。我蹲下去,轻轻拂过它的羽毛。
那天,父亲和我把鸡的遗体,带到江边,找到一棵榕树,埋葬了。回家路上,我在心里对它说:
下辈子投个好胎,不要再做鸡了。
黑啤酒酿鸡蛋
母亲从未试过彻夜不归,唯一的一次,带回来一条震撼的消息:
她的一位下属被杀了!
碎尸案!
我那天没去上幼儿园,看着母亲的几个要好同事,一大早来家里开会。她们虽没去现场,在家里同样辗转反侧。出了人命的大事儿,不是只在报纸里读到嘛,怎么还发生在自己身边呢?还是日日相处的同事!
母亲捧着茶过来了,脸上明显是刚从大风大浪中下来,还惊魂不定的样子。她以做会计的精密,尽量把案件的细节都一一讲述。
“阿英真惨,”母亲说。“案发前还刚和丈夫那个了。” 因为有我在场,母亲用“那个”指代房事。一圈女人互相看了看,都懂了,偷偷瞄了瞄圈子里的小不点。我却没有意识到母亲用了暗号,倒是想到另一个问题:”妈妈,我认识那个阿姨吗?“
”你见过一次,“母亲说,”就是肥肥的那个。“
我想了想,联想不起谁,没再纠缠下去。
母亲继续:“然后两公婆就去睡觉。谁知道她老公起来就把她勒死了,还用刀把两个胸切下来!”
裸露乳房的画面,一下展现在所有人面前。我看了看四周的阿姨,每个人的脸都发青了,嘴巴因为惊恐而半张开,像失去呼吸。
“那个男的守着一堆肉,过了三天三夜。后来臭了,怕邻居发现,就去自首了。”
“那他有没有说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一个阿姨探过头问。
这个阿姨我倒认识,给我做过很好吃的通心粉。
“听那些警官说,他自己很后悔,说都是黄色录影带惹得祸。”
“啧啧啧......”女人们嘴巴同时发出一样的声响,头也跟着摇起来。我在旁边推断,她们也许是惋惜,也许是害怕。
“哇!你们都不知道!那些警官多犀利!”案情说完,母亲开始炫耀她的首个通宵,“晚晚熬夜都精神!说喝的都是黑啤加生鸡蛋。”
“真的?”
大家顿时都忘记了血腥,被一只鸡蛋撩起兴趣了。
“恩!我亲眼看到,鸡蛋在里面熟了。”
母亲最后还强调了一句:“很补的!”
这宗命案,在母亲和同事参加完追悼会回来,便和日子一起消散了。那个给我做过通心粉的阿姨,后来和母亲闹不和,过年连利是都不给了,就不用想通心粉了。
我长大后,明白了什么是“那个”,也多了一项在喝酒时可以炫耀的资本:
“你们知道吗? 黑啤可以煮熟鸡蛋呢!”
会自杀的狗
回头看,大学刚毕业那一年,是我偏离阳光大道的开始。而所有的征兆,原来始于一只自杀了的小狗。
我毕业找工作找得很晚,所以找地方住也找得晚。好室友就像工作一样,都提前被挑走了。最后剩下别人介绍的一个男孩,是学校里读商学系的。一起去看房子那天,觉得男孩不像强奸犯,而且房子也不错,一个下午就签了合同,R成了我的男性室友。
我在雀巢工作,一次超市里卖咖啡时,认识一个小姑娘,挺聊得来。临分别,小姑娘提到她有一只小狗,想送人。我自己一直想养狗,短信问R,他也同意,便约了一个周末碰面,交接狗狗。
狗狗叫乐乐。小姑娘说。我们在北京四环外的一个城乡超市碰面。乐乐小得像条虫子,身子蠕蠕的,从一个陌生人传到另一个陌生人手里。各取所需了,准备说拜拜。我和R问有什么要注意的,小姑娘说没有,就走了。
我和R就像刚有了宝宝的新手父母,啥都不懂。不晓得去买狗粮,也不晓得给乐乐安置一个窝。傻乐傻乐捧回家,饿了给喂点牛奶,只顾着轮流和小狗玩。乐乐倒也不介意,迈开小短腿,在地板上奔跑。木地板很旧了,一脚踩过,后面跟着几根掉出来。地上也很脏,两个还未学会持家的年轻人,不知道从何开始。但乐乐的身体很白,白得让人爱不惜手。
乐乐更喜欢我,也许是家中唯一一个发出母性气味的人吧。别人一抱他就叫着跑了,我一抱,小脑袋一个劲往我怀里钻,呼噜呼噜睡着了。我不是爱幻想生孩子的人,但和另一个有心跳有体温的动物贴在一起,我突然觉得自己成了妈妈。
养了大概一周后,乐乐不知道为什么,开始突然抽搐。就像人的癫痫,一下倒在地上,全身打颤。嘴里还发出“呜呜”的声音,听起来很痛苦。抽了一会,乐乐自己站起来,像没事一样。但乐乐开始不怎么喝牛奶了,蔫蔫地靠在墙角,或者就呆在我怀里。那时候度娘还没问世,比较熟悉电脑的R才想起要去谷歌。搜索结果显示,乐乐应该得了病。
赶紧问那个小姑娘,她回信说乐乐挺健康的呀。那去看兽医。R说等周末吧。
周五,我一早去上班了。在堆成山的咖啡纸皮箱里,我收到了R的短信:
乐乐跳楼自杀了。
什么?
R出门上班,走到楼下,听见“砰“的一声,上前一看,乐乐躺在一片血泊里。
“一定是从阳台上跳下去的。"R说。
我想起那个阳台,看房子时一眼相中。还未发展成烧烤娱乐之地,却先成为案发现场。
“那乐乐呢?”
“我把它扔进垃圾桶,就去上班了。” 西装革履的R,拍拍手去上班了。
晚上,我下班经过楼下,抬头看到遮挡自行车的塑料棚上,果然破出一个洞,洞的形状,和乐乐的体型相仿。
它解脱了。
一针麻醉剂
感觉还没在时差里站稳,我们就要面对P需要做紧急手术的现实。
医生一再保证,这不是什么大手术。但我还是慌,又恼又慌。不是本来好好来度假吗?怎么就成了要进手术室呢?还是全麻的!
先生问我要不要回家照顾一老一小,我想了想,还是决定留下来。看不见面,可以想象的空间越多。布生同意,说随时保持联系,晚点带住院需要的衣服来。
P也许累了,或者他知道前方有一把手术刀在等着他。说不清楚的情绪,一下像火球一样爆发出来,在地上又哭又踢脚。劝服已经听不进去了,我只能又是拉又是扯,像狠心的屠夫,怀里兜着一只挣扎逃命的小动物。
麻醉师和护士都在二楼等了,可是P动得像满身是刺,无从下手。我好想像发了疯一样吼起来,把心中的无奈与无助,借助嘴巴呕出来。但房间太安静了,眼前的人也安静,只能用手,轻轻抚摸P害怕的头发。
等了很久,瑞典护士说,要不下一小时再做手术吧。我坚决不同意,生怕再晚点,就有生命危险了。护士于是拿来一个小恐龙玩偶,我心里有点厌恶,想这个小东西,能起什么作用?
也许P哭累了,他看了看玩偶,嘶叫渐渐转成呜咽,到最后,停了。大家都像愿望成真一样庆幸,赶紧抓紧机会,叫我抱着他进麻醉室,把袖子卷起来。
“这是什么呀?”护士问。
“恐龙。”P说。
“你喜欢恐龙吗?”
“恩。”
麻醉师一针下去。
啪!
P一直拽在手里的小车子,和新拿的小恐龙,一起掉在地上。
我才知道,原来麻醉药的威力如此大,大得叫人恐惧。手里实实在在的一个人,比眨眼还快,就只剩下一具没有思想的空壳。我习惯性的想起最坏的结局,可无论怎么想,我都接受不了。心就像被怪物咀嚼一样,难受得不能呼吸。
听说死神在梦中来临时,会过来把人招走。我把P放在床上,咬着泪水,在他耳边说:
宝贝,无论谁来,你都不要跟他走,知道吗?答应妈妈!
P睡着的样子,还是那么甜美。
那应该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长的一小时。我像一只游魂,走廊上无目的徘徊。护士看到我了,出来把我撵到等候室。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里默默重复祈祷的话。人靠不住时,只能靠神仙了。
P出来了。我一眼看到脱去的裤子,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脚边。移动的床,带起血腥的味道。我闭着呼吸,想逃避。
床被推到观察室,护士替P插上心跳监控机。滴答,滴答,规律得像走在钢丝线上,我好害怕突然会掉下来。
护士说等药醒了,就可以去病房。我趴在P的旁边,手用力捏他的肉。
快醒醒,我的宝贝,快醒醒。
没有反应。
快醒醒,求你了,一定要醒过来。
小拇指动了一下。
醒了,醒了!护士,他醒了!
P像从很深的水中游出来,揉了揉眼睛,又回到水里。
我摸了摸胸口,口头还了欠下各路神仙的人情,心像踏在水泥地上的双脚,终于安稳了。
姜
因为炎热,家里的姜没放几天就开始长出嫩芽。正好那几天我心血来潮要种东西,腾出一个花盘,把姜埋在土地里。
过了几天我去视察,发现嫩芽已经舒适张开了。它往空去的土地发展,大手大脚张罗自己的地盘。
生命里真旺盛啊!我想。再看看种的其他花与香草,全都顶不住热带大雨,苗都还没站稳就被打趴下去了。 我想这大概也是姜廉价的原因,怎么种怎么都成活,民间就叫做下贱的作物。兰花那么精贵,肯定就是娇滴滴,需要天气,肥料,还要每天摘叶除虫,很久才冒出那么一朵来。
知道姜适应能力那么强,我也没再怎么去打理。而且种东西的热情过了,每天经过花盘也懒得蹲下来。该活的会活下来的。
大概又过了几星期,一天早上,我刚醒还模模糊糊,决定去看看绿色植物,清醒清醒。竹子和芭蕉还是那个样,叶子黄了又抽出绿叶。我扒着泥土去寻觅那块姜,原来的芽不仅长成了嫩姜,还好几个呢。一个串一个,看着就觉得舌头上泛起甜丝丝的辣。
我继续扒拉,像看看种下去的那块,长成什么样?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终于在那排新姜旁边,看到皱巴巴的,失去了光泽的姜皮。我推断,那就是原来的那块。我用手戳了戳,老去的皮下面,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了。
我突然明白,所谓生死,就是最终,一切化为尘土,滋润养育下一代。而眼前的轮回,不知道为什么,让人莫名感动。
我想,我不再害怕死亡了。
■ 节选自作者的每日书,本文编辑李依蔓

郑重声明:本站所有内容均来自互联网,旨在传播更多的信息,版权为原作者所有。若有不合适的地方,请联系本站删除,邮箱:599385753@qq.com。
下一篇:一个汉中90后的中秋节印象